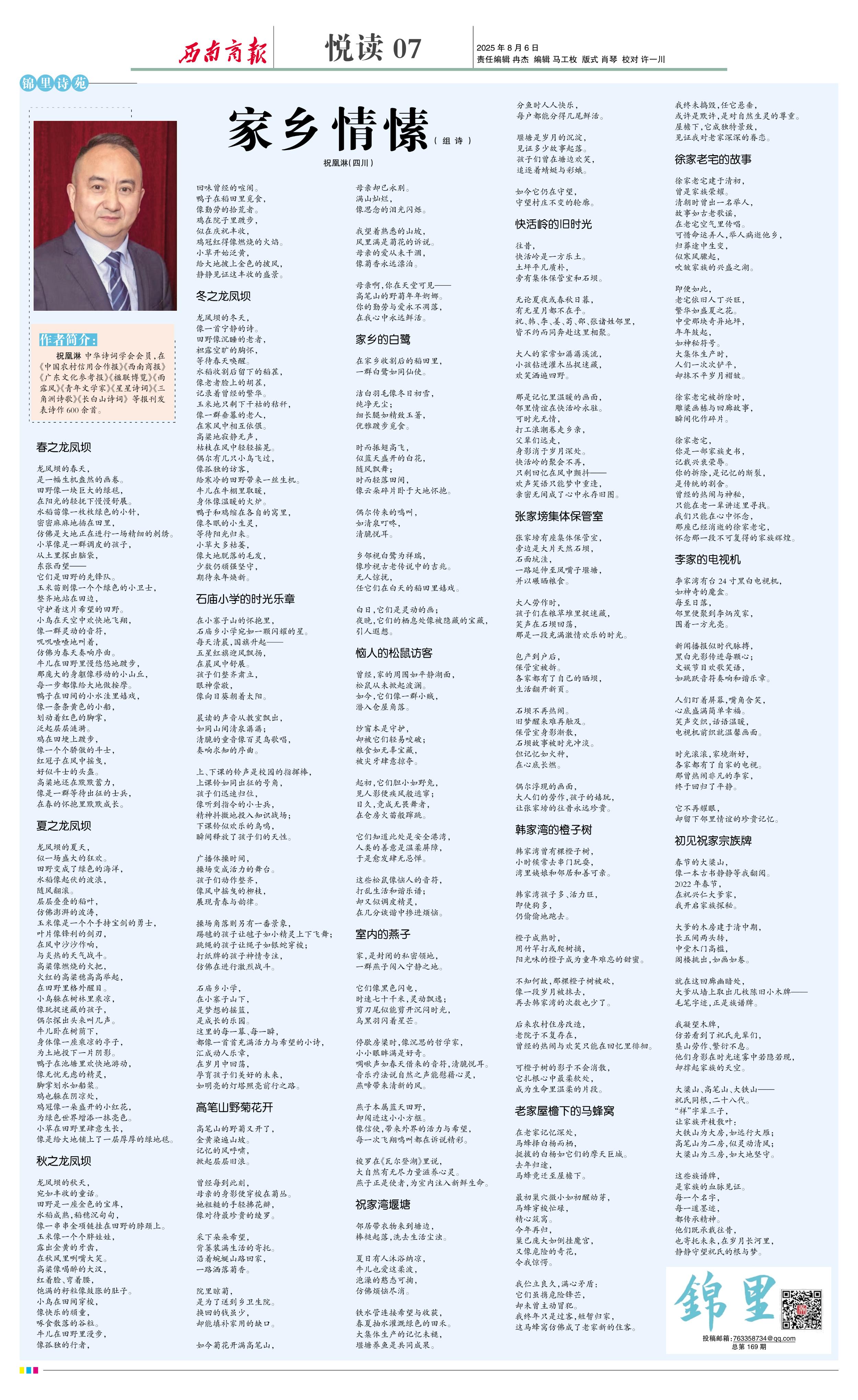本版导读
家乡情愫(组诗)
文章字数:4,188
祝凰淋(四川)
作者简介:
祝凰淋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在《中国农村信用合作报》《西南商报》《广东文化参考报》《楹联博览》《雨露风》《青年文学家》《星星诗词》《三角洲诗歌》《长白山诗词》等报刊发表诗作600余首。
春之龙凤坝
龙凤坝的春天,
是一幅生机盎然的画卷。
田野像一块巨大的绿毯,
在阳光的轻抚下慢慢舒展。
水稻苗像一枚枚绿色的小针,
密密麻麻地插在田里,
仿佛是大地正在进行一场精细的刺绣。
小草像是一群调皮的孩子,
从土里探出脑袋,
东张西望——
它们是田野的先锋队。
玉米苗则像一个个绿色的小卫士,
整齐地站在田边,
守护着这片希望的田野。
小鸟在天空中欢快地飞翔,
像一群灵动的音符,
叽叽喳喳地叫着,
仿佛为春天奏响序曲。
牛儿在田野里慢悠悠地踱步,
那庞大的身躯像移动的小山丘,
每一步都像给大地做按摩。
鸭子在田间的小水洼里嬉戏,
像一条条黄色的小船,
划动着红色的脚掌,
泛起层层涟漪。
鸡在田埂上踱步,
像一个个骄傲的斗士,
红冠子在风中摇曳,
好似斗士的头盔。
高粱地还在默默蓄力,
像是一群等待出征的士兵,
在春的怀抱里默默成长。
夏之龙凤坝
龙凤坝的夏天,
似一场盛大的狂欢。
田野变成了绿色的海洋,
水稻像起伏的波浪,
随风翻滚。
层层叠叠的稻叶,
仿佛澎湃的波涛,
玉米像是一个个手持宝剑的勇士,
叶片像锋利的剑刃,
在风中沙沙作响,
与炎热的天气战斗。
高粱像燃烧的火把,
火红的高粱穗高高举起,
在田野里格外醒目。
小鸟躲在树林里乘凉,
像玩捉迷藏的孩子,
偶尔探出头来叫几声。
牛儿卧在树荫下,
身体像一座乘凉的亭子,
为土地投下一片阴影。
鸭子在池塘里欢快地游动,
像无忧无虑的精灵,
脚掌划水如船桨。
鸡也躲在阴凉处,
鸡冠像一朵盛开的小红花,
为绿色世界增添一抹亮色。
小草在田野里肆意生长,
像是给大地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绿地毯。
秋之龙凤坝
龙凤坝的秋天,
宛如丰收的童话。
田野是一座金色的宝库,
水稻成熟,稻穗沉甸甸,
像一串串金项链挂在田野的脖颈上。
玉米像一个个胖娃娃,
露出金黄的牙齿,
在秋风里咧嘴大笑。
高粱像喝醉的大汉,
红着脸、弯着腰,
饱满的籽粒像鼓胀的肚子。
小鸟在田间穿梭,
像快乐的顽童,
啄食散落的谷粒。
牛儿在田野里漫步,
像孤独的行者,
回味曾经的喧闹。
鸭子在稻田里觅食,
像勤劳的拾荒者。
鸡在院子里踱步,
似在庆祝丰收,
鸡冠红得像燃烧的火焰。
小草开始泛黄,
给大地披上金色的披风,
静静见证这丰收的盛景。
冬之龙凤坝
龙凤坝的冬天,
像一首宁静的诗。
田野像沉睡的老者,
袒露空旷的胸怀,
等待春天唤醒。
水稻收割后留下的稻茬,
像老者脸上的胡茬,
记录着曾经的繁华。
玉米地只剩下干枯的秸秆,
像一群垂暮的老人,
在寒风中相互依偎。
高粱地寂静无声,
枯枝在风中轻轻摇晃。
偶尔有几只小鸟飞过,
像孤独的访客,
给寒冷的田野带来一丝生机。
牛儿在牛棚里取暖,
身体像温暖的火炉。
鸭子和鸡缩在各自的窝里,
像冬眠的小生灵,
等待阳光归来。
小草大多枯萎,
像大地脱落的毛发,
少数仍顽强坚守,
期待来年焕新。
石庙小学的时光乐章
在小寨子山的怀抱里,
石庙乡小学宛如一颗闪耀的星。
每天清晨,国旗升起——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在晨风中舒展。
孩子们整齐肃立,
眼神崇敬,
像向日葵朝着太阳。
晨读的声音从教室飘出,
如同山间清泉潺潺;
清脆的童音像百灵鸟歌唱,
奏响求知的序曲。
上、下课的铃声是校园的指挥棒,
上课铃如同出征的号角,
孩子们迅速归位,
像听到指令的小士兵,
精神抖擞地投入知识战场;
下课铃似欢乐的鸟鸣,
瞬间释放了孩子们的天性。
广播体操时间,
操场变成活力的舞台。
孩子们动作整齐,
像风中摇曳的柳枝,
展现青春与韵律。
操场角落则另有一番景象,
踢毽的孩子让毽子如小精灵上下飞舞;
跳绳的孩子让绳子如银蛇穿梭;
打纸牌的孩子神情专注,
仿佛在进行激烈战斗。
石庙乡小学,
在小寨子山下,
是梦想的摇篮,
是成长的乐园。
这里的每一幕、每一瞬,
都像一首首充满活力与希望的小诗,
汇成动人乐章,
在岁月中回荡,
孕育孩子们美好的未来,
如明亮的灯塔照亮前行之路。
高笔山野菊花开
高笔山的野菊又开了,
金黄染遍山坡。
记忆的风呼啸,
掀起层层旧浪。
曾经每到此刻,
母亲的身影便穿梭在菊丛。
她粗糙的手轻拂花瓣,
像对待最珍贵的绫罗。
采下朵朵希望,
背篓装满生活的寄托。
沿着蜿蜒山路回家,
一路洒落菊香。
院里晾菊,
是为了送到乡卫生院。
换回的钱虽少,
却能填补家用的缺口。
如今菊花开满高笔山,
母亲却已永别。
满山灿烂,
像思念的泪光闪烁。
我望着熟悉的山坡,
风里满是菊花的诉说。
母亲的爱从未干涸,
像菊香永远漂泊。
母亲啊,你在天堂可见——
高笔山的野菊年年婀娜。
你的勤劳与爱永不凋落,
在我心中永远鲜活。
家乡的白鹭
在家乡收割后的稻田里,
一群白鹭如同仙使。
洁白羽毛像冬日初雪,
纯净无尘;
细长腿如精致玉箸,
优雅踱步觅食。
时而振翅高飞,
似蓝天盛开的白花,
随风飘舞;
时而轻落田间,
像云朵碎片卧于大地怀抱。
偶尔传来的鸣叫,
如清泉叮咚,
清脆悦耳。
乡邻视白鹭为祥瑞,
像珍视古老传说中的吉兆。
无人惊扰,
任它们在白天的稻田里嬉戏。
白日,它们是灵动的画;
夜晚,它们的栖息处像被隐藏的宝藏,
引人遐想。
恼人的松鼠访客
曾经,家的周围如平静湖面,
松鼠从未掀起波澜。
如今,它们像一群小贼,
潜入仓屋角落。
纱窗本是守护,
却被它们轻易咬破;
粮食如无辜宝藏,
被尖牙肆意掠夺。
起初,它们胆小如野兔,
见人影便疾风般逃窜;
日久,竟成无畏舞者,
在仓房火苗般蹿跳。
它们知道此处是安全港湾,
人类的善意是温柔屏障,
于是愈发肆无忌惮。
这些松鼠像恼人的音符,
打乱生活和谐乐谱;
却又似调皮精灵,
在几分诙谐中掺进烦恼。
室内的燕子
家,是封闭的私密领地,
一群燕子闯入宁静之地。
它们像黑色闪电,
时速七十千米,灵动飘逸;
剪刀尾似能剪开沉闷时光,
乌黑羽闪着星芒。
停歇房梁时,像沉思的哲学家,
小小眼眸满是好奇。
啁啾声如春天借来的音符,清脆悦耳。
音乐疗法说自然之声能慰藉心灵,
燕啼带来清新的风。
燕子本属蓝天田野,
却闯进这小小方框。
像信使,带来外界的活力与希望,
每一次飞翔鸣叫都在诉说精彩。
梭罗在《瓦尔登湖》里说,
大自然有无尽力量滋养心灵。
燕子正是使者,为室内注入新鲜生命。
祝家湾堰塘
邻居带衣物来到塘边,
棒槌起落,洗去生活尘浊。
夏日有人沐浴纳凉,
牛儿也爱这柔波,
泡澡的憨态可掬,
仿佛烦恼尽消。
铁水管连接希望与收获,
春夏抽水灌溉绿色的田禾。
大集体生产的记忆未褪,
堰塘养鱼是共同成果。
分鱼时人人快乐,
每户都能分得几尾鲜活。
堰塘是岁月的沉淀,
见证多少故事起落。
孩子们曾在塘边欢笑,
追逐着蜻蜓与彩蛾。
如今它仍在守望,
守望村庄不变的轮廓。
快活岭的旧时光
往昔,
快活岭是一方乐土。
土坪平凡质朴,
旁有集体保管室和石坝。
无论夏夜或春秋日暮,
有无星月都不在乎。
祝、韩、李、姜、苟、邵、张诸姓邻里,
皆不约而同奔赴这里相聚。
大人的家常如潺潺溪流,
小孩钻进灌木丛捉迷藏,
欢笑洒遍四野。
那是记忆里温暖的画面,
邻里情谊在快活岭永驻。
可时光无情,
打工浪潮卷走乡亲,
父辈们远走,
身影消于岁月深处。
快活岭的聚会不再,
只剩回忆在风中颤抖——
欢声笑语只能梦中重逢,
亲密无间成了心中永存旧图。
张家塝集体保管室
张家塝有座集体保管室,
旁边是大片天然石坝,
石面坑洼,
一路延伸至凤嘴子堰塘,
并以碾晒粮食。
大人劳作时,
孩子们在粮草堆里捉迷藏,
笑声在石坝回荡,
那是一段充满激情欢乐的时光。
包产到户后,
保管室被拆。
各家都有了自己的晒坝,
生活翻开新页。
石坝不再热闹。
旧梦醒来难再触及。
保管室身影渐散,
石坝故事被时光冲淡。
但记忆如火种,
在心底长燃。
偶尔浮现的画面,
大人们的劳作,孩子的嬉玩,
让张家塝的往昔永远珍贵。
韩家湾的橙子树
韩家湾曾有棵橙子树,
小时候常去串门玩耍,
湾里姨娘和邻居和善可亲。
韩家湾孩子多、活力旺,
即使狗多,
仍偷偷地跑去。
橙子成熟时,
用竹竿打或爬树摘,
阳光味的橙子成为童年难忘的甜蜜。
不知何故,那棵橙子树被砍,
像一段岁月被抹去,
再去韩家湾的次数也少了。
后来农村住房改造,
老院子不复存在,
曾经的热闹与欢笑只能在回忆里徘徊。
可橙子树的影子不会消散,
它扎根心中最柔软处,
成为生命里温柔的片段。
老家屋檐下的马蜂窝
在老家记忆深处,
马蜂择白杨而栖,
挺拔的白杨如它们的摩天巨城。
去年归途,
马蜂竟迁至屋檐下。
最初巢穴微小如初醒幼芽,
马蜂穿梭忙碌,
精心筑窝。
今年再归,
巢已庞大如倒挂魔宫,
又像危险的奇花,
令我惊愕。
我伫立良久,满心矛盾:
它们虽携危险锋芒,
却未曾主动冒犯。
我终年只是过客,短暂归家,
这马蜂窝仿佛成了老家新的住客。
我终未捣毁,任它悬垂,
或许是默许,是对自然生灵的尊重。
屋檐下,它成独特景致,
见证我对老家深深的眷恋。
徐家老宅的故事
徐家老宅建于清初,
曾是家族荣耀。
清朝时曾出一名举人,
故事如古老歌谣,
在老宅空气里传唱。
可惜命运弄人,举人病逝他乡,
归葬途中生变,
似寒风骤起,
吹皱家族的兴盛之湖。
即便如此,
老宅依旧人丁兴旺,
繁华如盛夏之花。
中堂那块奇异地坪,
年年鼓起,
如神秘符号。
大集体生产时,
人们一次次铲平,
却抹不平岁月褶皱。
徐家老宅被拆除时,
雕梁画栋与回廊故事,
瞬间化作碎片。
徐家老宅,
你是一部家族史书,
记载兴衰荣辱。
你的拆除,是记忆的断裂,
是传统的割舍。
曾经的热闹与神秘,
只能在老一辈讲述里寻找。
我们只能在心中怀念,
那座已经消逝的徐家老宅,
怀念那一段不可复得的家族辉煌。
李家的电视机
李家湾有台24寸黑白电视机,
如神奇的魔盒。
每至日落,
邻里便聚到李炳茂家,
围着一方光亮。
新闻播报似时代脉搏,
黑白光影传进每颗心;
文娱节目欢歌笑语,
如跳跃音符奏响和谐乐章。
人们盯着屏幕,嘴角含笑,
心底盛满简单幸福。
笑声交织,话语温暖,
电视机前织就温馨画面。
时光滚滚,家境渐好,
各家都有了自家的电视。
那曾热闹非凡的李家,
终于回归了平静。
它不再耀眼,
却留下邻里情谊的珍贵记忆。
初见祝家宗族牌
春节的大梁山,
像一本古书静静等我翻阅。
2022年春节,
在祝兴仁大爹家,
我开启家族探秘。
大爹的木房建于清中期,
长五间两头转,
中堂木门高槛,
阁楼挑出,如画如卷。
就在这回廊幽暗处,
大爹从墙上取出几枚陈旧小木牌——
毛笔字迹,正是族谱牌。
我凝望木牌,
仿若看到了祝氏先辈们,
垦山劳作、繁衍不息。
他们身影在时光迷雾中若隐若现,
却撑起家族的天空。
大梁山、高笔山、大铁山——
祝氏同根,二十八代。
“祥”字辈三子,
让家族开枝散叶:
大铁山为大房,如远行大雁;
高笔山为二房,似灵动清风;
大梁山为三房,如大地坚守。
这些族谱牌,
是家族的血脉见证。
每一个名字,
每一道墨迹,
都传承精神。
他们既承载往昔,
也寄托未来,在岁月长河里,
静静守望祝氏的根与梦。
作者简介:
祝凰淋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在《中国农村信用合作报》《西南商报》《广东文化参考报》《楹联博览》《雨露风》《青年文学家》《星星诗词》《三角洲诗歌》《长白山诗词》等报刊发表诗作600余首。
春之龙凤坝
龙凤坝的春天,
是一幅生机盎然的画卷。
田野像一块巨大的绿毯,
在阳光的轻抚下慢慢舒展。
水稻苗像一枚枚绿色的小针,
密密麻麻地插在田里,
仿佛是大地正在进行一场精细的刺绣。
小草像是一群调皮的孩子,
从土里探出脑袋,
东张西望——
它们是田野的先锋队。
玉米苗则像一个个绿色的小卫士,
整齐地站在田边,
守护着这片希望的田野。
小鸟在天空中欢快地飞翔,
像一群灵动的音符,
叽叽喳喳地叫着,
仿佛为春天奏响序曲。
牛儿在田野里慢悠悠地踱步,
那庞大的身躯像移动的小山丘,
每一步都像给大地做按摩。
鸭子在田间的小水洼里嬉戏,
像一条条黄色的小船,
划动着红色的脚掌,
泛起层层涟漪。
鸡在田埂上踱步,
像一个个骄傲的斗士,
红冠子在风中摇曳,
好似斗士的头盔。
高粱地还在默默蓄力,
像是一群等待出征的士兵,
在春的怀抱里默默成长。
夏之龙凤坝
龙凤坝的夏天,
似一场盛大的狂欢。
田野变成了绿色的海洋,
水稻像起伏的波浪,
随风翻滚。
层层叠叠的稻叶,
仿佛澎湃的波涛,
玉米像是一个个手持宝剑的勇士,
叶片像锋利的剑刃,
在风中沙沙作响,
与炎热的天气战斗。
高粱像燃烧的火把,
火红的高粱穗高高举起,
在田野里格外醒目。
小鸟躲在树林里乘凉,
像玩捉迷藏的孩子,
偶尔探出头来叫几声。
牛儿卧在树荫下,
身体像一座乘凉的亭子,
为土地投下一片阴影。
鸭子在池塘里欢快地游动,
像无忧无虑的精灵,
脚掌划水如船桨。
鸡也躲在阴凉处,
鸡冠像一朵盛开的小红花,
为绿色世界增添一抹亮色。
小草在田野里肆意生长,
像是给大地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绿地毯。
秋之龙凤坝
龙凤坝的秋天,
宛如丰收的童话。
田野是一座金色的宝库,
水稻成熟,稻穗沉甸甸,
像一串串金项链挂在田野的脖颈上。
玉米像一个个胖娃娃,
露出金黄的牙齿,
在秋风里咧嘴大笑。
高粱像喝醉的大汉,
红着脸、弯着腰,
饱满的籽粒像鼓胀的肚子。
小鸟在田间穿梭,
像快乐的顽童,
啄食散落的谷粒。
牛儿在田野里漫步,
像孤独的行者,
回味曾经的喧闹。
鸭子在稻田里觅食,
像勤劳的拾荒者。
鸡在院子里踱步,
似在庆祝丰收,
鸡冠红得像燃烧的火焰。
小草开始泛黄,
给大地披上金色的披风,
静静见证这丰收的盛景。
冬之龙凤坝
龙凤坝的冬天,
像一首宁静的诗。
田野像沉睡的老者,
袒露空旷的胸怀,
等待春天唤醒。
水稻收割后留下的稻茬,
像老者脸上的胡茬,
记录着曾经的繁华。
玉米地只剩下干枯的秸秆,
像一群垂暮的老人,
在寒风中相互依偎。
高粱地寂静无声,
枯枝在风中轻轻摇晃。
偶尔有几只小鸟飞过,
像孤独的访客,
给寒冷的田野带来一丝生机。
牛儿在牛棚里取暖,
身体像温暖的火炉。
鸭子和鸡缩在各自的窝里,
像冬眠的小生灵,
等待阳光归来。
小草大多枯萎,
像大地脱落的毛发,
少数仍顽强坚守,
期待来年焕新。
石庙小学的时光乐章
在小寨子山的怀抱里,
石庙乡小学宛如一颗闪耀的星。
每天清晨,国旗升起——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在晨风中舒展。
孩子们整齐肃立,
眼神崇敬,
像向日葵朝着太阳。
晨读的声音从教室飘出,
如同山间清泉潺潺;
清脆的童音像百灵鸟歌唱,
奏响求知的序曲。
上、下课的铃声是校园的指挥棒,
上课铃如同出征的号角,
孩子们迅速归位,
像听到指令的小士兵,
精神抖擞地投入知识战场;
下课铃似欢乐的鸟鸣,
瞬间释放了孩子们的天性。
广播体操时间,
操场变成活力的舞台。
孩子们动作整齐,
像风中摇曳的柳枝,
展现青春与韵律。
操场角落则另有一番景象,
踢毽的孩子让毽子如小精灵上下飞舞;
跳绳的孩子让绳子如银蛇穿梭;
打纸牌的孩子神情专注,
仿佛在进行激烈战斗。
石庙乡小学,
在小寨子山下,
是梦想的摇篮,
是成长的乐园。
这里的每一幕、每一瞬,
都像一首首充满活力与希望的小诗,
汇成动人乐章,
在岁月中回荡,
孕育孩子们美好的未来,
如明亮的灯塔照亮前行之路。
高笔山野菊花开
高笔山的野菊又开了,
金黄染遍山坡。
记忆的风呼啸,
掀起层层旧浪。
曾经每到此刻,
母亲的身影便穿梭在菊丛。
她粗糙的手轻拂花瓣,
像对待最珍贵的绫罗。
采下朵朵希望,
背篓装满生活的寄托。
沿着蜿蜒山路回家,
一路洒落菊香。
院里晾菊,
是为了送到乡卫生院。
换回的钱虽少,
却能填补家用的缺口。
如今菊花开满高笔山,
母亲却已永别。
满山灿烂,
像思念的泪光闪烁。
我望着熟悉的山坡,
风里满是菊花的诉说。
母亲的爱从未干涸,
像菊香永远漂泊。
母亲啊,你在天堂可见——
高笔山的野菊年年婀娜。
你的勤劳与爱永不凋落,
在我心中永远鲜活。
家乡的白鹭
在家乡收割后的稻田里,
一群白鹭如同仙使。
洁白羽毛像冬日初雪,
纯净无尘;
细长腿如精致玉箸,
优雅踱步觅食。
时而振翅高飞,
似蓝天盛开的白花,
随风飘舞;
时而轻落田间,
像云朵碎片卧于大地怀抱。
偶尔传来的鸣叫,
如清泉叮咚,
清脆悦耳。
乡邻视白鹭为祥瑞,
像珍视古老传说中的吉兆。
无人惊扰,
任它们在白天的稻田里嬉戏。
白日,它们是灵动的画;
夜晚,它们的栖息处像被隐藏的宝藏,
引人遐想。
恼人的松鼠访客
曾经,家的周围如平静湖面,
松鼠从未掀起波澜。
如今,它们像一群小贼,
潜入仓屋角落。
纱窗本是守护,
却被它们轻易咬破;
粮食如无辜宝藏,
被尖牙肆意掠夺。
起初,它们胆小如野兔,
见人影便疾风般逃窜;
日久,竟成无畏舞者,
在仓房火苗般蹿跳。
它们知道此处是安全港湾,
人类的善意是温柔屏障,
于是愈发肆无忌惮。
这些松鼠像恼人的音符,
打乱生活和谐乐谱;
却又似调皮精灵,
在几分诙谐中掺进烦恼。
室内的燕子
家,是封闭的私密领地,
一群燕子闯入宁静之地。
它们像黑色闪电,
时速七十千米,灵动飘逸;
剪刀尾似能剪开沉闷时光,
乌黑羽闪着星芒。
停歇房梁时,像沉思的哲学家,
小小眼眸满是好奇。
啁啾声如春天借来的音符,清脆悦耳。
音乐疗法说自然之声能慰藉心灵,
燕啼带来清新的风。
燕子本属蓝天田野,
却闯进这小小方框。
像信使,带来外界的活力与希望,
每一次飞翔鸣叫都在诉说精彩。
梭罗在《瓦尔登湖》里说,
大自然有无尽力量滋养心灵。
燕子正是使者,为室内注入新鲜生命。
祝家湾堰塘
邻居带衣物来到塘边,
棒槌起落,洗去生活尘浊。
夏日有人沐浴纳凉,
牛儿也爱这柔波,
泡澡的憨态可掬,
仿佛烦恼尽消。
铁水管连接希望与收获,
春夏抽水灌溉绿色的田禾。
大集体生产的记忆未褪,
堰塘养鱼是共同成果。
分鱼时人人快乐,
每户都能分得几尾鲜活。
堰塘是岁月的沉淀,
见证多少故事起落。
孩子们曾在塘边欢笑,
追逐着蜻蜓与彩蛾。
如今它仍在守望,
守望村庄不变的轮廓。
快活岭的旧时光
往昔,
快活岭是一方乐土。
土坪平凡质朴,
旁有集体保管室和石坝。
无论夏夜或春秋日暮,
有无星月都不在乎。
祝、韩、李、姜、苟、邵、张诸姓邻里,
皆不约而同奔赴这里相聚。
大人的家常如潺潺溪流,
小孩钻进灌木丛捉迷藏,
欢笑洒遍四野。
那是记忆里温暖的画面,
邻里情谊在快活岭永驻。
可时光无情,
打工浪潮卷走乡亲,
父辈们远走,
身影消于岁月深处。
快活岭的聚会不再,
只剩回忆在风中颤抖——
欢声笑语只能梦中重逢,
亲密无间成了心中永存旧图。
张家塝集体保管室
张家塝有座集体保管室,
旁边是大片天然石坝,
石面坑洼,
一路延伸至凤嘴子堰塘,
并以碾晒粮食。
大人劳作时,
孩子们在粮草堆里捉迷藏,
笑声在石坝回荡,
那是一段充满激情欢乐的时光。
包产到户后,
保管室被拆。
各家都有了自己的晒坝,
生活翻开新页。
石坝不再热闹。
旧梦醒来难再触及。
保管室身影渐散,
石坝故事被时光冲淡。
但记忆如火种,
在心底长燃。
偶尔浮现的画面,
大人们的劳作,孩子的嬉玩,
让张家塝的往昔永远珍贵。
韩家湾的橙子树
韩家湾曾有棵橙子树,
小时候常去串门玩耍,
湾里姨娘和邻居和善可亲。
韩家湾孩子多、活力旺,
即使狗多,
仍偷偷地跑去。
橙子成熟时,
用竹竿打或爬树摘,
阳光味的橙子成为童年难忘的甜蜜。
不知何故,那棵橙子树被砍,
像一段岁月被抹去,
再去韩家湾的次数也少了。
后来农村住房改造,
老院子不复存在,
曾经的热闹与欢笑只能在回忆里徘徊。
可橙子树的影子不会消散,
它扎根心中最柔软处,
成为生命里温柔的片段。
老家屋檐下的马蜂窝
在老家记忆深处,
马蜂择白杨而栖,
挺拔的白杨如它们的摩天巨城。
去年归途,
马蜂竟迁至屋檐下。
最初巢穴微小如初醒幼芽,
马蜂穿梭忙碌,
精心筑窝。
今年再归,
巢已庞大如倒挂魔宫,
又像危险的奇花,
令我惊愕。
我伫立良久,满心矛盾:
它们虽携危险锋芒,
却未曾主动冒犯。
我终年只是过客,短暂归家,
这马蜂窝仿佛成了老家新的住客。
我终未捣毁,任它悬垂,
或许是默许,是对自然生灵的尊重。
屋檐下,它成独特景致,
见证我对老家深深的眷恋。
徐家老宅的故事
徐家老宅建于清初,
曾是家族荣耀。
清朝时曾出一名举人,
故事如古老歌谣,
在老宅空气里传唱。
可惜命运弄人,举人病逝他乡,
归葬途中生变,
似寒风骤起,
吹皱家族的兴盛之湖。
即便如此,
老宅依旧人丁兴旺,
繁华如盛夏之花。
中堂那块奇异地坪,
年年鼓起,
如神秘符号。
大集体生产时,
人们一次次铲平,
却抹不平岁月褶皱。
徐家老宅被拆除时,
雕梁画栋与回廊故事,
瞬间化作碎片。
徐家老宅,
你是一部家族史书,
记载兴衰荣辱。
你的拆除,是记忆的断裂,
是传统的割舍。
曾经的热闹与神秘,
只能在老一辈讲述里寻找。
我们只能在心中怀念,
那座已经消逝的徐家老宅,
怀念那一段不可复得的家族辉煌。
李家的电视机
李家湾有台24寸黑白电视机,
如神奇的魔盒。
每至日落,
邻里便聚到李炳茂家,
围着一方光亮。
新闻播报似时代脉搏,
黑白光影传进每颗心;
文娱节目欢歌笑语,
如跳跃音符奏响和谐乐章。
人们盯着屏幕,嘴角含笑,
心底盛满简单幸福。
笑声交织,话语温暖,
电视机前织就温馨画面。
时光滚滚,家境渐好,
各家都有了自家的电视。
那曾热闹非凡的李家,
终于回归了平静。
它不再耀眼,
却留下邻里情谊的珍贵记忆。
初见祝家宗族牌
春节的大梁山,
像一本古书静静等我翻阅。
2022年春节,
在祝兴仁大爹家,
我开启家族探秘。
大爹的木房建于清中期,
长五间两头转,
中堂木门高槛,
阁楼挑出,如画如卷。
就在这回廊幽暗处,
大爹从墙上取出几枚陈旧小木牌——
毛笔字迹,正是族谱牌。
我凝望木牌,
仿若看到了祝氏先辈们,
垦山劳作、繁衍不息。
他们身影在时光迷雾中若隐若现,
却撑起家族的天空。
大梁山、高笔山、大铁山——
祝氏同根,二十八代。
“祥”字辈三子,
让家族开枝散叶:
大铁山为大房,如远行大雁;
高笔山为二房,似灵动清风;
大梁山为三房,如大地坚守。
这些族谱牌,
是家族的血脉见证。
每一个名字,
每一道墨迹,
都传承精神。
他们既承载往昔,
也寄托未来,在岁月长河里,
静静守望祝氏的根与梦。
发布日期:2025-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