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导读
面对未来的可能性
文章字数:1,5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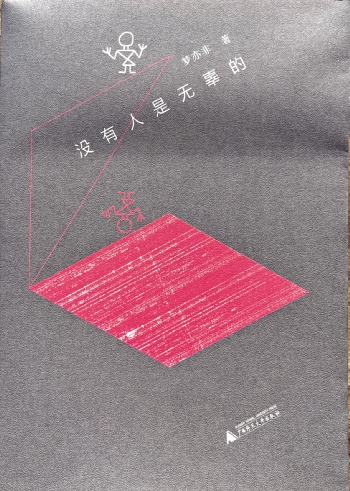
陈子弘(四川)
我们的首次相遇,是在2008年成都的一次诗歌聚会上。此前我从来没有见过梦亦非,只是听说过他的名字,但第一次见面似乎就有很熟悉的感觉,但那一次与他也只是礼节性地寒暄了一下。2018年后,他每次来成都我们都能相聚。他曾经说过,“文学品位一直在我身上蔓延,但我并不眷恋那些会过时的东西。”他的小说语言风格经常会让我联想到20世纪的许多小说家,单一的风格并不适合他,对复杂性的探索却是自然而睿智的。他认为,面对复杂性和未来的可能性,应该有一个使命。
对我来说,梦亦非第一印象的熟悉感、直接性和真实感吸引了我。对许多或大多数读者来说,这会大大增加对他的文学作品的好奇。从文学角度,到底梦亦非作品的哪些特质吸引了我?我有时也会感到困惑,他的经历相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复杂的,从在家乡的一行政单位负责人任上辞职、在独山老家山中潜心读书、四处游历、自己创业又跑到广州直到前几年把“群山之心”搞得风生水起;好多年前就有人说他声称不再用现代汉语写诗,但老梦之前用汉语写的东西确实已经很多很多了,当然我也只读过其中一小部分。他的所有小说中我彻底细读的是“碧城三部曲” —— 《碧城书》《没有人是无辜的》《迷宫与嬉戏》,这三部小说用梦亦非方式的后现代主义及后后现代主义手法重构了整个二十世纪的水族当代史。
我不太喜欢用先锋与实验这两个词来定位他这个“碧城三部曲”。梦亦非这个作品其实超越了“先锋”和“实验”这两个词的范畴,从多元融合性、自我反思、语言游戏性、身份探索及现实与虚构的模糊等多个方面有了更宽和更深的特点,这众多的特点熔于一炉,显示了他在后现代之后的语境中寻找身份与情感归宿的文学努力,展示了他自身对于现代社会、文化、科技和哲学问题的深入反思和探究。
梦亦非的中文诗写了这么多年,其成绩是有目共睹的,那些作品对很多读者来说依然可以带来兴奋和猜测,阅读的冲动依然可以在意想不到的地点用意想不到的方式涌现和表现出来,仍然令人着迷。一个作家的身份及其在家庭、社会、文化和文学传统中的地位在梦亦非的诗歌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对梦亦非来说,界定诗歌自我的方式首先是融入,其次是超越现代汉语诗的前辈的身份,找到多元文化的面貌。我想,梦亦非的最终姿态会是对文化习俗与当代汉语诗歌的所谓规则的勉强承认,尽管他会认为这些习俗和规则根本不可靠,但他的生活和写作又离不开这些习俗和规则的启发。
因为我与他都要写英文诗,梦亦非会把他写好的英文诗文本发给我看,我应该是第一读者,我也会很坦诚地提出一些在词法和句法上的修改意见。可以说我对他发给我的千余行英文诗句了如指掌。写英文诗的梦亦非绝非天真自发的诗人,而是一个博览群书、分析能力极强的人,而且越写越好。梦亦非今年初完成的长诗《幽灵当代史》编织了一幅关于记忆、失落和水族人不朽精神的缠绵画卷。诗歌中弥漫着怀旧情绪,幽灵们追忆着他们故乡的土地,如今这已成为遥远记忆。他们在祖先的声音中找到慰藉,这些声音在时间中回荡,敦促他们不要忘记。诗歌中充满了自然和传统的象征,从河流和山脉到文化遗产,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寻找身份。幽灵们化身为道路、博物馆,甚至大地本身,试图与自己的根重新建立联系。它们见证了时间的流逝以及抹去历史的无情进步。然而,他们坚持着,他们的本质与自然世界交织在一起,在时代的热浪中寻找一个巢穴,在混乱中寻找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
《幽灵当代史》弥漫着一种健康的怀旧情绪,这一切就像透过飞机或游轮舷窗看到的一样,短暂地照亮,然后退入记忆的世界。这不仅仅是一首诗,更是一次自我发现之旅,是“碧城三部曲”的进一步升华。梦亦非以一个游走于多种文化和语言之间的诗人的视角,通过选择用英语表达自己,他其实大胆地挑战了用汉语写作的诗歌表达的传统界限,为他对身份、语言和文化遗产的探索增添了另一层深度。他的刻意选择证明了诗人完全可以在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的同时,勇于尝试各种形式的勇气和意愿。
发布日期:2024-09-11



